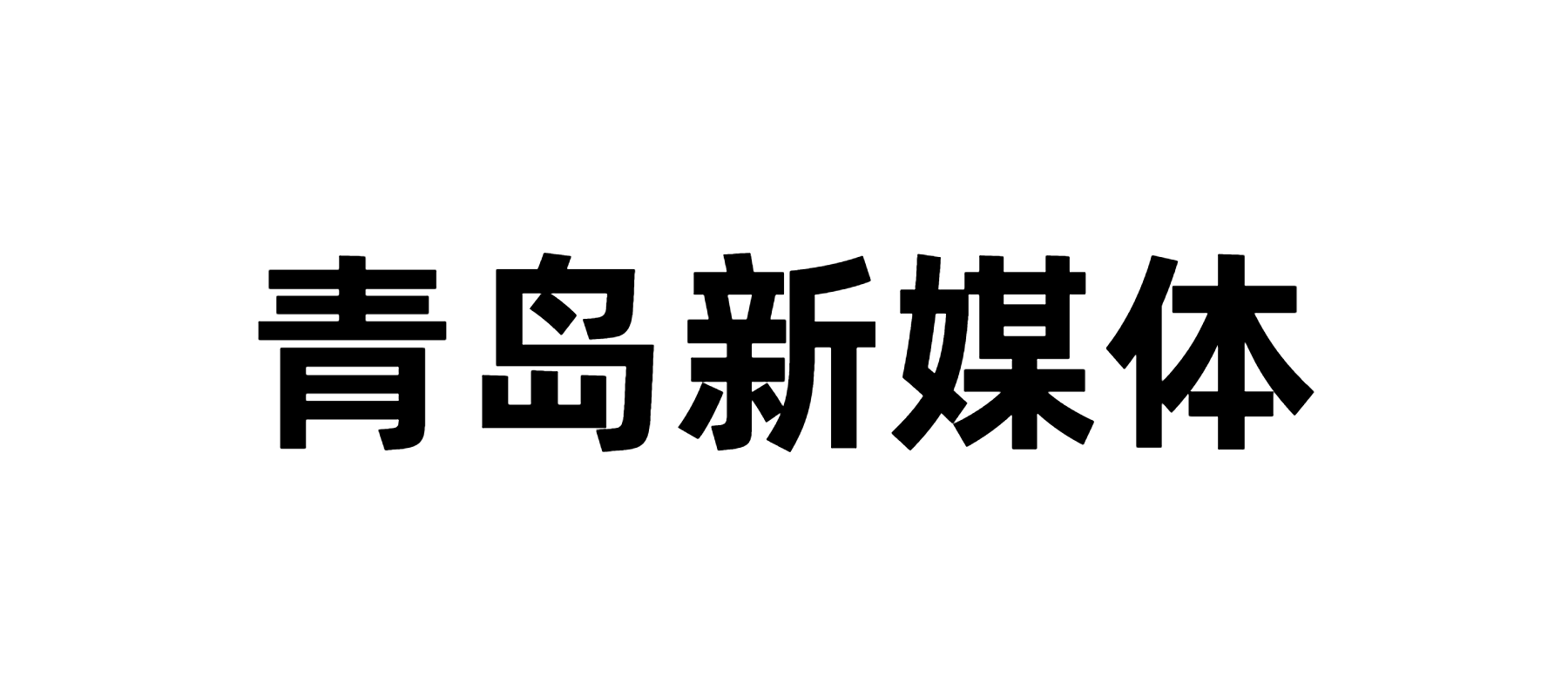从《春日偶成》谈二程理学 程准
北宋理学家、教育家,理学的奠基者,“洛学”代表人物程颢的《春日偶成》历来被视作一首闲适的写景小诗,然而,在其浅近通俗的语言背后,深藏着二程理学的哲学内核。本文旨在突破将理学简单等同于“存天理,灭人欲”的僵化叙事,通过对《春日偶成》的深度解读,论证二程理学,尤其是程颢一脉,其终极追求并非一个枯寂、无情的道德律令世界,而是一种“活泼泼地”、与物同体的生命境界与精神体验。是围绕“孔颜之乐”的承续、“天人一本”的体证、以及“德”与“乐”的圆融,《春日偶成》是二程理学“活的精神”的诗意呈现。
宋代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波澜壮阔的时期,理学(或称道学)的兴起为其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石。程颢、程颐兄弟,世称“二程”,是这一思潮的奠基者。他们构建了以“天理”为核心的哲学体系,其“存天理,灭人欲”的命题在后世的传播与解读中,常常被简化为一种严苛的、禁欲主义的道德教条,使得理学家的形象往往被定格为“道貌岸然”、“冷冰冰”的卫道士。然而,当我们翻开程颢的诗集,读到《春日偶成》这样清新明快的作品时,上述刻板印象便受到了强烈的冲击:
云淡风轻近午天,傍花随柳过前川。
时人不识余心乐,将谓偷闲学少年。
这首诗描绘了风和日丽的春日景色,抒发了诗人郊游时的愉快心情。如果隐去作者之名,我们或会以为这是某位田园诗人的即兴之作。但它的作者,正是一位深刻的理学家。这种“反差”恰恰是理解二程理学,特别是程颢思想的关键入口。本文认为,《春日偶成》并非程颢偶尔的“闲情逸致”,而是其理学思想在生命情境中的自然流露与诗意表达。它生动地诠释了二程理学所追求的最高境界——一种超越了世俗功利与感官欲望,在与天地万物的感通中获得的、内在自足的“乐”。这种境界,用理学自身的术语来说,正是“孔颜之乐”的宋代回响,是“天人一本”哲学观的切身证悟,是道德修养(德)与精神愉悦(乐)的高度统一。本文将通过对这首诗的层层剖析,试图还原一个更为丰满、鲜活且充满生命力的二程理学形象。
一、 “时人不识余心乐”:“孔颜之乐”的承续与升华
“乐”是《春日偶成》的诗眼,也是理解程颢理学境界的核心。他明确表示,这种“乐”是“时人”所无法理解的。那么,此“乐”究竟为何物?它并非源自物质享受或世俗成就,而是直指儒家思想中的一个古老而崇高的命题——“孔颜之乐”。
《论语》中记载,孔子赞叹颜回:“贤哉回也!一箪食,一瓢饮,在陋巷,人不堪其忧,回也不改其乐。”(《论语·雍也》)这种身处贫贱却“不改其乐”的精神状态,成为了后世儒者孜孜以求的境界。二程对此极为推崇。程颢说:“昔受学于周茂叔,每令寻颜子、仲尼乐处,所乐何事。”[1] 这表明,探寻“孔颜之乐”的本质,是二程学术生涯的起点与核心关怀。
在二程的哲学体系中,“孔颜之乐”的根源在于“天理”而非“人欲”。程颢说:“‘乐天知命’,通上下之言也。圣人乐天,则不须知命。知命者,知有命而信之者尔。‘乐天’者,如颜子之‘乐’,‘一箪食,一瓢饮,在陋巷,人不堪其忧,回也不改其乐。’箪瓢陋巷,何足乐?盖别有所乐以胜之耳。”[2] 此处的“别有所乐”,即是体认“天理”后所获得的精神超越与内在自足。当个体的生命与宇宙的普遍法则(天理)相契合时,外在环境的顺逆、物质生活的丰俭,便不再能动摇其内心的安宁与喜悦。
回到《春日偶成》,程颢所乐之事,表面上是“云淡风轻”、“傍花随柳”的自然美景,实质上,是他在此情此景中,真切地体证到了“天理”的流行发用。春天的生机勃发,万物和谐,正是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(《周易·系辞下》)这一“天理”最直观的显现。他的游赏,是一种哲学性的观照,是“随事观理则天下之理得矣”的实践。他在自然中看到了“理”的活泼与完美,从而内心充满了与之共鸣的欣悦。这种乐,是“道心”之乐,是“天理”之乐。因此,“时人不识”正在于此。“时人”仍停留在“人心私欲”的层面,用功利的、世俗的眼光来衡量一切,将程颢的行为理解为“偷闲学少年”的轻狂或懈怠。他们无法理解,一个理学家为何会因自然景致而如此沉醉。这恰恰揭示了“道心”与“人心”、“天理”与“人欲”之间的张力。程颢的“余心乐”,正是对“孔颜之乐”在宋代语境下的承续与升华,它将一种安贫乐道的品格,扩展为一种在任何情境下都能与“天理”相融、从而无入而不自得的精神境界。
二、 “云淡风轻”与“傍花随柳”:“天人一本”的体证与境界
《春日偶成》的前两句,不仅写景,更蕴含着程颢独特的宇宙观。与程颐更注重“性即理”的内在超越路径有所不同,程颢更强调“仁者浑然与物同体”[3]的体验式境界。他的“天人合一”观,是“一本”的,而非“合一”的。他曾直言:“天人本无二,不必言合。”[4] 这意味着,人与自然界在本质上就是一体相连的,并非两个独立实体后再去寻求结合。在这一哲学视野下,重新审视“云淡风轻近午天,傍花随柳过前川”,我们便能读出更深层的意蕴。“云淡风轻”:这不仅是天气描述,更是“理”之“中和”状态的象征。云不过浓,风不过猛,一切恰到好处,这正是程颐所言的“中者,无过无不及之谓也”[5]在自然中的体现。程颢观此景,即是观“理”。“傍花随柳”:这四个字极具动感与情感。诗人不是冷漠的观察者,而是亲切地“傍”着花,“随”着柳,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,毫无隔阂。这生动地实践了他的“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,莫非己也”[3]的思想。花柳不再是外在的客体,而是与自身生命息息相关的的一部分。“近午天”与“过前川”:诗中“近”与“过”二字,巧妙地传达了诗人因沉醉于与天地精神的往来而忘却时间、忘却路途的忘我状态。这与庄子“游心于物之初”的境界有异曲同工之妙,但根基不同。庄子的忘我是与“道”的冥合,是出世的;程颢的忘我则是与“仁”(天理)的感通,是即世而超越的。他并未脱离人伦物理,而是在人伦物理中证悟天理。
这种“天人一本”的体证,使得程颢的理学世界充满了生命的温度与情感的厚度。对他而言,“理”不是抽象思辨的逻辑结点,而是弥漫于天地之间、可以切身感受和体验的生生之意。他在《秋日偶成》中亦写道:“万物静观皆自得,四时佳兴与人同。”万物各得其理,四时变化与人的情感息息相通。这种“观物”方式,是一种充满仁爱和审美意味的直觉体悟,而非纯粹的逻辑分析。
因此,《春日偶成》中的春日郊游,实则是程颢一次深刻的哲学实践和修养功夫。他在与自然的亲密接触中,印证了“天人本无二”的真理,感受到了“仁”体的流行。这远非简单的“偷闲”,而是一种高级的“识仁”功夫。程颢教导学生时强调“学者须先识仁”[3],而《春日偶成》正是他本人“识仁”后精神境界的诗意写照。
三、 “德”与“乐”的圆融:理学境界的完成与展现
在二程理学中,道德修养(德)与精神境界(乐)并非割裂的两端,而是相辅相成、圆融统一的。严格的道德律令(“敬”)是入门功夫,而最终指向的则是一种从容、和乐的生命状态(“乐”)。《春日偶成》完美地展现了这种“德”与“乐”的圆融。
首先,二程将“成德、成圣”视为人生的根本目标。程颢说:“‘德不孤,必有邻’,一德立而百善从之。”[6] 程颐也说:“凡学之道,正其心、养其性而已。中正而诚,则圣矣。”[7] 修养的过程,即是“灭私欲则天理明”[8]的过程。这看似严苛,但其目的并非让人成为一个无情无欲的道德机器,而是为了破除“私意”的遮蔽,让本心与天理相通,从而获得真正的自由与快乐。
程颢的“乐”,正是建立在其深厚的德行修养基础之上的。没有对“私欲”的克制与对“天理”的持守,他便无法如此纯粹地、毫无滞碍地感受自然之美,并与之一体相通。一个蝇营狗苟于名利之人,即使面对再美的春光,其内心也难以产生如此澄明、自足的喜悦。他的“乐”,是“德立”之后“百善从之”的自然结果,是“天理明”后心灵本然状态的呈现。
其次,诗中体现了“敬”与“和”的统一。二程非常重视“敬”的修养功夫。程颢说:“‘居处恭,执事敬,与人忠’,此是彻上彻下语,圣人无此语。”[9] “敬”是一种内心专一、严肃认真的态度。然而,程颢所达到的“乐”的境界,并非时刻紧绷的“敬”,而是由“敬”入“和”,内心充盈着平和、舒泰与生机。春天的“云淡风轻”,正是他内心“中正而诚”后所呈现的“和”之气的外在投射。他的行为,既符合“敬”的修养,又达到了“和”的境界,这正是儒家理想人格——“温而厉,威而不猛,恭而安”——的体现。
最后,诗中的程颢,展现了一个“活生生”的理学家形象。他既恪守儒家的道德规范,又是一个情感丰富、热爱生活的“人”。他嘲笑“时人”的不解,带着一丝“孤芳自赏”的高雅,这并非傲慢,而是对自身所信奉之“道”的自信与坚守。这让我们看到,二程理学所追求的圣人,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祇,而是在日常生活中,能够“即其所居之位,乐其日用之常”[10]的坦荡君子。他们既有“中心如自固,外物岂能迁”[11]的道德定力,也有“傍花随柳过前川”的生活情趣。这种道德与情感、严肃与活泼的完美结合,才是二程理学希望达成的完整人格。
结论:通过对《春日偶成》的层层剖析,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,这首看似平淡的小诗,实则是打开二程理学,尤其是程颢思想宝库的一把钥匙。它有力地反驳了将理学简单等同于禁欲主义与道德教条的片面看法。
在诗中,我们看到了二程所探寻的“孔颜之乐”,如何从经典的文本走入现实的生命,成为一种在体认“天理”后获得的、超越世俗的精神愉悦。我们看到了程颢“天人本无二”的哲学观,如何转化为“傍花随柳”的亲切体验,使得抽象的“理”在活泼泼的自然生机中变得可感可触。最终,我们看到了严格的道德修养(德)与圆融的精神境界(乐)如何达成完美的统一,一个理学家既可以恪守“敬”的功夫,也能享受“和”的从容与生机。
《春日偶成》如同一幅微型的哲学画卷,它将二程理学中抽象的“天理”、“仁”、“诚”、“敬”等概念,融化在一个鲜活的生命场景之中。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漫步春日的诗人,更是一位践行其哲学理念的理学家。他通过这首诗告诉我们:“理”不在遥远的经典故纸堆中,而在“云淡风轻”的日常自然里;“圣”不是高高在上的偶像,而是能够体认自然、内心充盈、德行高贵的生命状态。 这种将高深哲理与平凡生活完美融合的境界,正是二程理学,尤其是程颢一脉思想,历久弥新的魅力所在,也是二程理学留给后世最宝贵的精神遗产之一。
参考文献
[1] 《二程遗书·卷二上》
[2]《二程遗书·卷十一》
[3]《二程遗书·卷二上》(“识仁篇”)
[4]《二程遗书·卷六》
[5]《二程遗书·卷七》
[6]《二程外书·卷十二》
[7]《二程遗书·卷二十五》
[8]《二程遗书·卷二十四》
[9]《二程遗书·卷二上》
[10]朱熹:《四书章句集注·中庸章句》
[11]程颢诗《秋日偶成》句
作者简介:
程 准,字四平,号别样红,憩云斋斋主;北宋理学家、教育家、儒家学派代表人、理学创立人程颐夫子二十九世孙;世程联家谱委委员、中华诗词学会会员、中国楹联学会会员、山东省文促会理学专委会副会长兼常务副秘书长、烟台市诗词学会会员、烟台市楹联家协会会员。发表论文《二程理学与齐鲁文化的关系浅析》;创作《海阳秧歌扭起来》《里口之歌》《里口版成都》等流行歌曲;编写《程氏世谱海阳里口谱系》《里口村志》;编有《程四平诗选》,诗联作品散见媒体、期刊。2016年荣获《中华文艺》全国文学创作大赛三等奖并入选中华文艺名人榜,作品选录在《中华文艺全国文学大赛获奖作品精选》。2017年荣获“当代知名诗人”“当代诗词名家”称号,作品入选《当代知名诗人诗选》《中国文学名家》。2020年对联作品入编《中国对联作品集2019年卷》,2025年对联作品入编《中国楹联传世精品典藏第三部》。
本网信息来自于互联网,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,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。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,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、文字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,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。本站不承担此类作品侵权行为的直接责任及连带责任。如若本网有任何内容侵犯您的权益,请及时联系我们,本站将会在24小时内处理完毕。:https://www.gji.yztytoyf.com/6874.html